最后一个“克林索尔”

托格涅· 林德格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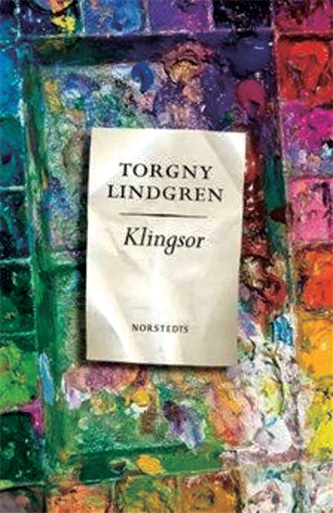
《克林索尔》
我们的世界是世俗的,但应该也是艺术的;是繁华的,但应该也是寂寞、清冷的。人类过于迅猛和草率的生存和那些缓慢的若有所思的生命在根本上没有差别。有问题的是我们,我们太着急慌忙,只因和那些石头相比,人类的生命太短促。在这故事里,主人公克林索尔愿做“死亡了的物质的传信人”,“和表浅的生命抗衡”。
自从发现了森林里一个斜树桩上的玻璃杯,克林索尔就将它背负了一生,背成了一个画家的人生信条和使命:没有什么是死了的。他不打算画出什么漂亮图画,只想从平凡和倾斜,从无生命中揭示他看到过的最深处的生命精华。
作家林德格伦认为,没有什么能区分生和死。死去的物质只是以更缓慢的速度活着。人类过于迅猛和草率的生存和那些缓慢的若有所思的生命在根本上没有差别。有问题的是我们,我们太着急慌忙,只因和那些石头相比,人类的生命太短促。他希望读者慢慢咀嚼这个被写得发展缓慢、还应更慢的故事。在这故事里,主人公克林索尔愿做“死亡了的物质的传信人”,“和表浅的生命抗衡”。
《克林索尔》是托格涅· 林德格伦在2014年出版的小说。作家于1938 年出生在瑞典北方小城西博腾郊外。遵从父母意愿做了教师。1965年作为诗人登上文坛。1982年因小说《岩上的蛇道》收获巨大成功,此后创作了一系列以故乡为背景的当代经典。1991年,林德格伦当选瑞典学院院士。
西博腾的“克林索尔”
一座西博腾森林里待售的旧屋,克林索尔家的旧屋;透过窗户,“我们”看得见屋外的山峦,山外还是山,连绵不断。“我们”的身份和人数不明,儿时看过的克林索尔画展曾让 “我们”吃惊地睁大眼睛,受到震动,如今有心追踪他的足迹,找到更多证据陈述他的伟大。表面看,“我们”对克林索尔传奇的追问成就了《克林索尔》。对他的勾画来自“我们”的回忆,“我们”对克林索尔本人、妹妹和乡民的采访,也来自克林索尔和他的函授老师、后来的妻子芳妮的书信。
为何采用“我们”而不是“我”?林德格伦说:过了75岁再写“我”深感疲劳;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理由是,在克林索尔的时代,那些谈绘画、论艺术的书通常采用“我们”;“我们”是“我和读者”的混合。三点理由虚实兼备,有情绪的、有理性的。显而易见,读者随“我们”的视线追踪了一个让“克林索尔传奇”从支离破碎到基本成形的过程。
小说声称,书名不是来自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那篇表现印象派画家生命最后历程的故事《克林索尔的最后一个夏天》,也非出自德国音乐家瓦格纳最后的歌剧《帕西法尔》。在黑塞的小说里,克林索尔是个画家,他的作品在亲近朋友的小圈子里活着,他的故事特别是最后一个夏天的传奇也活着;而在瓦格纳的歌剧里,克林索尔是个耽于淫欲又一心想接近“圣杯”,加入圣杯骑士团的人,而那里的成员首先是要求纯洁,克林索尔给自己施了宫刑,不但未达目的反而遭到放逐,抱着仇恨和野心,他转而投向魔法。林德格伦深受德国文学艺术影响,无论是托马斯·曼还是黑塞和瓦格纳都和他有深入的精神交流。因而,尽管本文没有篇幅分析三个克林索尔的关联,仍需指出,将黑塞和瓦格纳的表达当作林德格伦所阐述的艺术人生的“史前史”也不为过。
林德格伦乐于给笔下的人物安排离奇古怪的命运,这次,他给克林索尔派了个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当兵的祖先,“克林索尔”这个姓就是那瑞典兵从德国北部吕贝克附近一座墓园的碑石上看来的。士兵觉得自己受洗的名和家族的姓凑在一块毫无特色,想拿“克林索尔”替换,得到上司的同意;士兵进而提出添上个凸显贵族气的字符“冯”,被上司怒斥:“你好大的胆子!”然而,这个“冯”字竟真被克林索尔的后人们偶尔把玩着,在画家克林索尔的签名里也会冒出来。
一只玻璃杯引出的人生使命
10岁出头的某一天,在森林中,小克林索尔看到一块斜斜的树桩上站着一只泛绿色的玻璃酒杯。后来发现,这杯子和家里其他的几只很像——那是祖父遗忘的。
老克林索尔有酿酒绝招,每年五旬节这一天,春色正好,他会把藏了一冬的酒拿出来,独自走向森林。他在那里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直到数日后,最后一滴酒也早已喝尽,他才会往家走,重启程式化的日常生活,憧憬着来年的这一时日。最后一次,他把酒杯遗忘在了森林里。
当小克林索尔将这只让爷爷酣醉过的杯子带回家,放于平坦的桌面时,杯子反而歪斜了,失去了在树桩上的平衡。在斜树桩上的很多年里,杯子一直试图像一只体面的酒杯那样挺直胸膛。它长期去适应树桩的斜面——它的生存环境,它一直活着。这只既倾斜又平直、既丑陋又闪烁出异常光泽的杯子将存在之光照射到小克林索尔的心上,点亮了他的感知。他看见杯里舞动的生命,看到万物有灵,死了的活着;他感觉到艺术的启示,更听到了召唤:他的使命就是将那感知到的,死了的物质深处的生命表现出来。
玻璃杯是个引人联想又十分费解的意象。多少受着《圣经》哺育的瑞典读者不难想到“圣杯”,甚至不难想到作家哈瑞·马丁松的《阿尼阿拉》,在那组长诗的第十三首,提到人类乘坐的飞船是上帝精魂玻璃碗中的一个小气泡,若玻璃碗久不被碰,气泡会缓缓移动。老克林索尔的杯子不被碰到已经很久,或许内部就有个气泡在缓缓运行的途中。
得到启示的克林索尔开始接受绘画函授教育。在居于南方大城市马尔默的女教师芳妮的远程指点下,克林索尔开始作画,只画静物。
芳妮问:“在你所有的画上总有个歪斜的玻璃酒杯,有时在背景里,有时是作为前景, 遮蔽了那些其他的对象,而哪怕在阴影中,它也还是被最清楚地照射的那一个。真有这必要吗?像我前面说的,玻璃杯可从来都不直。”他回答:“没错,这绝对必要。”
他在给芳妮的信中说:“这里没人能理解我或是深入到我的想法里去。”某种程度上,他对此感到庆幸:“理解是一个人走错路的标识。那个能被他人理解的人是站不住脚的,无价值的。” “我获得了一个启示,”他继续写道:“一个启示和现象,打开了我的双眼,看到现实内部的本质。用艺术的形式把我一度所看到的告知更多的大众,这是我的使命。”芳妮并不理解他: “努力在你的平庸和好笑的想法上构筑你的艺术生活吧。”克林索尔读这回信时,窗外是被霜笼罩了的土豆田,没有人透过窗户看到他的内心。

